為什麼孩子不說話?破除「選擇性緘默症」的迷思與三大刻板印象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首先要挑戰的刻板印象是,選擇性緘默症只發生於童年時期。第二個要挑戰的刻板印象是,選擇性緘默症只發生在學校。第三個刻板印象是,大多數、或甚至全部的選擇性緘默孩童都曾被虐待。
文:卡爾・薩頓(Carl Sutton)、雪莉兒・弗雷斯特(Cheryl Forrester)
挑戰選擇性緘默症的迷思與刻板印象
我首先要挑戰的刻板印象是,選擇性緘默症只發生於童年時期。事實上,它可能延續至成人。本書的選擇性緘默者可以作為見證,包括十幾歲的青少年,還有從二十歲出頭到接近六十歲的成人。我的研究顯示,選擇性緘默症如果延續至成人,嚴重程度通常在二十歲出頭達到最高峰。不過,也有一些人直到五十多歲仍有重大的社交和說話困難,甚至與較年輕時相比並未減輕。至於五十多歲以後的資料則少之又少。
第二個要挑戰的刻板印象是,選擇性緘默症只發生在學校。根據我的研究,它其實發生在各式各樣的情境中:和陌生人、老師、同儕、醫師、牙醫、叔叔阿姨、祖父母、繼父繼母,甚至少數人對著父母也無法說話。
第三個刻板印象是,大多數、或甚至全部的選擇性緘默孩童都曾被虐待。這當然是錯的,應該不必多加解釋。遺憾的是,社會大眾卻仍普遍認為選擇性緘默症是疏忽或虐待直接造成的。這個誤解源於過去緘默總被形塑為心理創傷的必然結果。因此,有些為孩子盡心盡力的父母,仍得面對老師或其他人不公平的偏見和質疑。
茱莉亞寫出了身為家長的經驗,老師指責她女兒的選擇性緘默症是她的錯:
我們私下與老師會談。老師說:「妮琪小時候一定發生過什麼事。」在我聽來,她就是間接地指責我虐待孩子。
那位老師還說,我送女兒進學校時從不親吻她。他們以為一切都是我的錯,這令我很震驚。其他家長都不想和我說話了。
茱莉則寫了以下的經驗:
和我們不熟的人經常大聲地問我:「當時她發生了什麼事?」賈絲汀也聽到了。他們以為我會說出什麼可怕的事情,讓我們美麗的女兒突然從此不能說話。其實什麼事也沒有。
滿分的、充滿愛的家長也可能有選擇性緘默的兒女。質疑他們對待小孩的方式,無疑是可惡的。引發選擇性緘默症的因素,經常是無法解釋的,和/或者是芝麻小事(至少從大人的觀點來看是如此)。
並沒有證據顯示,選擇性緘默的孩子比一般孩子更可能、或更不可能遭受過虐待或情感傷害。
在此引用英國選擇性緘默症資訊與研究協會(Selective Mutism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Association)的斯拉金和史密斯的話:
有些家庭中存有較複雜的問題,若有懷疑,應介入處理。假設所有的個案/或絕對沒有個案遭受虐待或者情感傷害,都是常見的錯誤。
既然選擇性緘默症是焦慮障礙,當然可能因引發焦慮的生活經驗而惡化。事實上,許多干擾或破壞性的生活經驗,都會加劇孩童或青少年的選擇性緘默症狀況,包括:搬家、父母爭執或離婚、父母有心理疾病、失去親人、霸凌、恥辱,和感覺自己與別人不一樣等。本書便舉出了各種實際例子。
其他可能造成選擇性緘默症的環境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孤立,例如:孩子在第一次上學之前,與別人互動的機會太少。
當孩子置身於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需要面對外語的環境時(比如住在英國倫敦的日本小孩),也可能發展出選擇性緘默症。
選擇性緘默症是一種保持安靜的強迫行為
許多小孩面對陌生人而感到焦慮、覺得脆弱或危險,或者和主要照顧者分離時,都會出現保持緘默的強迫行為,這是正常反應,並非選擇性緘默的小孩所特有。當這種行為持續超過學校生活的初期,或引起嚴重的人際互動困難時,才會診斷為選擇性緘默症。因此,小孩開始上學的第一個月被排除於正式診斷標準之外,而僅視為轉換情境的緘默反應,通常持續不到一個月。選擇性緘默症通常會持續好幾年,而非幾個月。在實務上,有經驗或者瞭解辨認方法的人,很容易做診斷。其實很簡單,選擇性緘默者在某些情境之下無法說話。
從演化的觀點來看,遭受威脅時保持緘默,只是為了避免引起獵食者的注意所採取的退縮行為。儘管人類發展出了精緻的文明,但是畢竟我們仍然都是動物。學者將選擇性緘默類比為動物「凍住」(freeze)的防衛反應。根據我的經驗,我同意對年幼的孩子而言,選擇性緘默症感覺起來的確如此。小時候,我對於某些人保持緘默,並非經由思考或出於什麼想法,那完全是「刺激」(威脅性人物靠近)和「反應」(保持安靜)的運作。
叢林裡的動物一發現飢餓的獵食者逼近時,便立刻變得安靜且小心翼翼。同樣地,選擇性緘默的孩子亦出於自動和潛意識的機制,本能地採取緘默來躲避威脅,雖然他們所感知的威脅是來自於易受傷和被注意,而非被吃掉的危險。選擇性緘默的孩子並非刻意選擇保持緘默,而是當他們在身體、情緒或心理上感受威脅時,反擊或逃跑的本能反應便迫使他們緘默。因此,「被注意」(例如:暴露於人際互動情境)與緘默反應之間有直接的連結。同樣地,與主要照顧者分離也直接和緘默連結,因為分離帶來了危機和不適感,對於幼童尤其如此。
根據以上選擇性緘默症根本原因的描述,它並不需要任何壓力或創傷事件來加以引發。有些小孩先天的氣質,便是較易受到暴露與脆弱感的影響,自閉症和焦慮傾向的小孩尤其如此。
緘默的牢籠——從我的經驗談起
根據我的經驗,在某些人聽得到的範圍之內,我絕不可能說話。只要他們靠近,我就感到一股無法承受的壓力,並且陷入緘默的牢籠。即使他們只不過出現在房間的另一端,我也感到私人的空間受到侵害。光是想到他們可能聽到我的聲音,便令我不知所措。
對於選擇性緘默的小孩(或大人)而言,說話可能是非常親密、令人緊張、困窘和備感威脅的舉動。選擇性緘默的小孩通常傾向於迴避風險,而保持靜默通常讓他們感到比較安全。他們的感受如此強烈,以至於在具有威脅的情境中,開口說話簡直難如登天。我的經驗是,只要說出一個字就好像將把我整個內在世界的鑰匙交給別人,向他們暴露出我的思想、感情、缺乏、欲望和需求。分享這些事情,總是令我感到非常不舒服。
即使我終於真的能夠與某些人輕鬆相處,我依舊無法和他們說話。雖然我通常很想講話,但我就是無法跨越說話的障礙。我小時候,對於保持緘默的原因覺得高深莫測,不瞭解自己為何不開口。現在回想起來,主要原因似乎是某些人原本就會引發我無比的壓力,我害怕說話會再度引起他們注意。只要我不說話,我就很安全。如果我開口了,就又得經歷壓力,而每一次感受到的壓力都會比以往更嚴重。我當然非常想要避免改變,尤其當改變可能會引起別人的注意或審視。
選擇性緘默的孩子或大人一旦保持靜默一段時間,周遭的人便開始不再期待他們開口說話。既然別人除了靜默別無期待,於是開口說話的恐懼(說話模式的牢籠)益發加深,一想到說話就覺得難上加難。在別人完全沒有預期之下開口,就好像自己是藏在盒子裡的彈簧玩偶,蓋子打開突然跳出來向每個人說:「驚喜!」而當初的緘默正是由這些人所引發的。
或許必須親身經歷過選擇性緘默症,才能瞭解受困於緘默的牢籠有多麼痛苦。 然而,一般人的誤解更增添這份痛苦。人們認為緘默是自己的選擇,是自己「拒絕說話」,因此鮮少給予同情和支持。事實上,沒有比這個看法錯得更離譜的了。
有時候,說話行為等於「分離」和「依附」行為
我先前描述過緘默、威脅和分離的關聯,當幼童面對威脅或與照顧者分離時,保持緘默完全是自然的反應。似乎有許多選擇性緘默的孩童,也同時有分離焦慮和/或依附障礙。事實上,有些學者將選擇性緘默形容為「缺乏安全感的依附行為」。
在此以實際例子(至少從我的經驗來看),說明說話行為與依附行為的關聯。我熟悉的人若和他們的親戚或其他有關係的人一起出現,總會引發我的緘默。例如:因為和繼父同住,我變成無法跟媽媽說話;我朋友的伴侶或朋友如果在場,我就無法開口;女兒的未婚夫或朋友也會引發我的緘默;在岳母或太太的朋友面前,我無法和太太講話。只有當在場的第三者與我熟悉的人沒有關係,我才能說話。尤其成人以後,如果第三者與「依附對象」完全沒有關係,我大概可以和他們說話,例如來我家修熱水器的工人。
因此,我這方面的說話行為呈現「三角形模式」:一個角是我自己,另一個角是依附對象,第三個角則是與依附對象有關係的人。我內省之後覺得,似乎我一方面預期「暴露於人際互動情境」(因而需要依附對象的支持),另一方面又預期當半熟不熟的人在場,我會「失去依附對象」。
上述三角形模式也可以解釋所謂的「進行性選擇性緘默症」(progressive mutism),它是選擇性緘默症的一種形式,會讓人逐漸退步直到無法跟任何人說話。我小時候,緘默的行為持續擴散與惡化,因為我不但無法克服對第三者的緘默,也變得長期無法和依附對象說話。譬如我弟弟結婚時,我無法和他太太說話,連帶地也從此無法跟他講話。小時候,未來的繼父搬來同住時,我也從此停止和媽媽說話。當我無法對某人說話,我也就沒辦法對任何與他有關係的人講話。因此,很快地,緘默便擴散至我生命中幾乎所有的人。
直到現在,每當面對類似的三角形模式時,我還是會強烈感受到停止說話的強迫意念。
我並不認為上述三角形模式,存在於每一個選擇性緘默的大人或小孩的身上。但是我相信,這的確相當常見。本書第十三章有一位家長露易絲也寫到她女兒的三角形模式。我們可以說,「悄悄融入」(Sliding-in)這個治療技巧便是直接針對三角形模式而設計的。這個方法是循序漸進地將引發緘默的第三者,融入孩子和他信任的人之間的情緒空間,從而建立信任關係。
「悄悄融入」的治療技巧是美琪・強生和艾莉森・溫特琴斯所提出。大致的方法是由孩子無法說話的一個對象(例如:老師),逐漸移動至進入聽得見孩子聲音的範圍(例如:由半開的門外聽到)。孩子由自己信任且可以說話的人陪同,整個過程都小聲地數著數字。關於「悄悄融入」以及其他治療技巧的詳細步驟,請參閱《選擇性緘默症資源手冊》第十章。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靠著對我媽媽朗讀一本書開始恢復和她說話,剛開始只是耳語,漸漸增加了音量,直到可以使用正常聲音。這個過程類似另一個治療技巧,叫做「塑型」(shaping)。「悄悄融入」和「塑型」都遵循了「漸進暴露」與「去除恐懼」的原則。
對於像我一樣無法與父母/繼父母說話的孩子,父母離婚是常見的經歷。當然,離婚本身就是家庭環境中莫大的焦慮來源。接著,若父親或母親再婚或交男、女朋友,更是直接將陌生人帶進了孩子的個人空間,使得原已很焦慮的孩子更難承受。對於原本就是選擇性緘默的孩子,這種情況可能非常煎熬,尤其當繼父或繼母又充滿控制欲或敵意。但是我必須說明,即使是最善良、最溫和的繼父母,要與選擇性緘默的孩子建立關係進而彼此交談,也是極為困難的。在父母離婚之前,我已長期受選擇性緘默症之苦,他們離婚又使我的狀況大幅惡化。
相關書摘 ▶這些有苦說不出的靈魂:「選擇性緘默症」,一種選擇不了的沉默焦慮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為什麼孩子不說話?:選擇性緘默症,一種選擇不了的沉默焦慮》,寶瓶文化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卡爾・薩頓(Carl Sutton)、雪莉兒・弗雷斯特(Cheryl Forrester)
譯者:黃晶晶
「不說話」,容易被誤會只是害羞、故意作對、很跩、沒禮貌⋯⋯在長期遭誤解、輕視,甚至霸凌下,孩子失去了自信,無法好好上學,交不到朋友。其實,它可能由先天敏感特質引發、受環境劇烈變動影響,而且並非長大就會好,甚至可能衍生更嚴重的焦慮和憂鬱,跟著人一輩子。理解和接納,讓被封印的聲音破繭而出。
選擇性緘默症是極隱性的病症,從鑑定到醫治,心理諮商、語言治療及特教系統等協助資源極少。而透過本書的數十位選擇性緘默者、家長、老師及專業心理師,在學習、工作、家庭、社會與人際領域的生命故事分享,我們瞭解到循序漸進地建立信任,將有機會助其走出恐懼與焦慮。愈是有口難言,愈需要用心理解、接納,才能在黑洞般的沉默中,找到珍貴的溝通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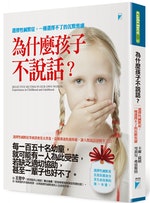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Tags:
【路怒狂徒的崛起-專題之前】或許臺灣行人最大的敵人不是車,而是人?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臺灣人本交通的發展到底碰到了什麼瓶頸?或許,成為真正的「人本城市」之前,我們不只需要硬體改造,還需要更多民眾的主動參與、凝聚共識,在生活中一步步養成重視「人」的城市文化。
2022年底,國際媒體報導臺灣交通有如行人地獄(living hell),引起社會一陣輿論風暴。回想當時,隨處可見以「人本交通」為題的社論文章,社群網站中也有不少人主動分享街道觀察與留學經驗,提出具體的改善建議,呼籲政府採取行動。
然而,其實各縣市政府一直陸陸續續有在推行道路品質提升、人行道增設等改善計畫,從劃設標線、好發事故路口改造,再到道路相關法規的修正都有所觸及。但是,當我們翻開道安資訊查詢網的統計數據,去年1月至10月的事故件數與前三年同期平均增長12.6%、死亡人數成長近2%;再點閱全國近五年交通事故趨勢分析圖,每月平均事故總件數仍高達三萬多件。
這些數字讓人不禁好奇,臺灣人本交通的發展到底碰到了什麼瓶頸?
臺灣交通糾結難解的結
曾主持多項道安改善研究計畫的陽明交大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教授吳昆峯坦言,「我們很多政策推到最後,會發現問題根源都是『停車』。」他直言,其實不是政府不願意動,而是民眾的反彈超乎想像。
「像是每個人都認同小朋友安全上下課很重要,但你仔細觀察,幾乎只有學校圍牆旁邊有人行道。為什麼?」他搖搖頭,「只要工程經過住家,就會有人抗議:我的門口要停車。然後找來里長、議員幾次周旋,很多計畫就這樣不了了之。」
但是,城市興建人行道怎麼會是由民意主導?更何況,現實中因少數居民反對而推動失敗的案例更是不勝枚舉。吳昆峯表示,雖然車輛停放是根本問題之一,但停車問題不只與道路規劃息息相關,它還涉及經濟成本、交通觀念、生活習慣等社會層面。他認為,政府必須提出短、中、長期的願景規劃與溝通策略,並運用小規模的示範建設,讓民眾看見改變,才有機會潛移默化的改變風氣,真正的解決問題。
過去幾年,他及系上的教授們共同帶領研究團隊,展開如車道寬度、行穿線退縮、行人庇護島、路口車道配置等多項交通研究,並致力推動國內道路交通工程設計規範的調整,如提出車道瘦身、擴大街角改善方案等,就是想藉由扎實的本土研究基礎,向上影響法令規範,推動臺灣往人本城市邁進的腳步。

除此之外,吳昆峯認為中央道路主管機關也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就像先有路,我才能規劃公車路線。中央要先有清楚的方向和明確的做法,地方才能跟上落實。」因此,他認為後續行政院對交通議題的重視與否,將是該組織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
狂徒崛起,是想讓更多人看見問題
其實,從停車問題就可以看出城市發展的公共性。城市沒有辦法、也不可能僅僅因為少數人制定的決策而改變。不論是人本還是車本,核心都是「一群」都市人形成的共同文化,若臺灣想要朝向人本城市更進一步,我們最需要的,還是養成重視「人」的生活文化。
這就是路怒狂徒崛起的初衷。喚起大家對議題的認知,認識自己、開啟對話,刺激人們主動關心議題的發展。所以,我們從生活中捕捉了各種對立的、矛盾的觀念,用情緒化的文字製作遊戲,希望讀者從答案中看見真實的自己,並在趣味之餘反思選項背後的意涵。當未來看見類似議題時,就能有更多的同理,一步一步改變整座城市的文化。
臺灣即將於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屆時每5人就有1位高齡者,人行環境的重要性將呈指數上升。或許現在你我正值體力充沛的青壯年,但再過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以人為本的行人環境真的不重要嗎。人本城市還多遠,答案取決於有多少人在意我們的城市環境。每多一個人留心、每多一份生活想像,我們與人本城市的距離就更進一步。
自己究竟有沒有想像中那麼「人本」?現在就點擊圖片測驗看看!










